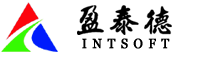火狐体育全站app:
他开着钢铁巨鸟,飞过雪山,穿过戈壁,尤其是川西那片叫“黑龙山脉”的鬼门关,他来来飞了不下百十趟。
十年前,一张“原发性高血压”的诊断书,像一只无形的大手,硬生生把他从万米高空拽了下来,死死地摁在了地上。
他回了老家,一个靠着黑龙山脉的川西小城,用一切的积储和补助,开了家无人机公司。
实际上,便是个体户,事务也便是帮人测绘个山林,给楼盘拍个宣传片,有时分还接点给人婚礼跟拍的活儿。
便是从镇上大喇叭和黑白电视里,听到了414航班在黑龙山脉失踪,国家派出很多人力物力搜救无果的英雄事迹。
从那时起,他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,他要当飞行员,要去天上看看,要去那片吞人的山里闯一闯。
他爹,范老根,一个老实巴交的林场工人,便是当年第一批被征召进山当导游的搜救队员。
公司事务越来越欠好干,新出来的年青人都玩高科技,设备比他的好,嘴巴比他的甜,价格比他的低。
“范老板,你这飞机是好,可续航仍是短了点,咱们那儿新找的公司,用的都是最新的氢燃料电池,能飞一下午呢!”
他仅仅默默地把他的“老伙计”拆解,装箱,然后发起他那辆开了十多年的破皮卡,慢吞吞地回了家。
老婆估量又在牌馆“筑长城”,孩子在外地读大学,偌大的屋子,冷锅冷灶,只要他一个人。
落日正在落下,把山脊染成了一片怪异的金赤色,巨大的山影,像一头缄默沉静的洪荒巨兽,爬行在地平线上,光是看着,就让人心里发慌。
他灌了一口啤酒,冰凉的液体顺着嗓子流下去,没尝到麦芽的香,只觉得一阵苦涩。
像一架飞不动的老飞机,停在机库的角落里,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的零件一个个老化,锈蚀,最终变成一堆谁都瞧不上的废铁。
相片现已泛黄,上面,是二十多年前的他,穿戴一身笔挺的飞行服,和几个相同年青的战友勾肩搭背,站在一架巨大的运输机前,笑得没心没肺。
他从戎是一个宿舍的兄弟,外号“顺风耳”,由于他对无线电那套东西有种天然生成的灵敏。
退役后,这小子没回东北老家,托关系进了川西一个鸟不拉大便的深山无线电监测站,一干便是十几年,俩人上一次联络,仍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
姜启明的声响,压得极低,带着一股子压抑不住的激动和惊骇,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相同。
“比让熊瞎子撵了还邪乎!”姜启明短促地喘着气,布景音里,是一阵“滋啦滋啦”的电流声。
“今天下午,咱们站里那台早就该进博物馆的旧式军用短波接收器,他娘的自己响了!”

“千真万确!我还给你录下来了!”姜启明的声响都在颤栗,他压低声响,简直是在用气声说话。
“那飞行员的呼号,他的口音,还有信号里那阵古怪的布景噪音……都跟三十年前空难陈述里记载的状况,一模相同!”
“他说那是太阳耀斑活动引起的电磁串扰,是正常现象!还他娘的让我明日写一份关于‘设备老化导致误判’的查看陈述!”
“可你不相同啊!你飞过那片山!你爹还进去过!那当地有多邪门,你比谁都清楚!”
“我还用站里的旧式测向仪大约定位了信号源,就在黑龙山脉内地,一个叫‘阎王愁’的山沟邻近!”
“阎王愁”三个字,像一把生锈的钥匙,了范卫国回忆最深处的锁眼里,然后“咯吱”一声,拧开了。

一个被父亲用生命符号的禁地,和一个来自三十年前的“鬼信号”,居然他娘的重合到了一块儿。
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用电脑把姜启明发过来的那段不到一分钟的音频,插着耳机,听了整整一夜。
他没告知任何人,开着他那辆破皮卡,拉着他公司里最精巧的那台“翼龙-3”工业级无人机,直接开到了间隔“阎王愁”山沟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公营林场。
无人机的摄像头里,传回的是一片一望无垠的原始林海,和很多刀削斧劈一般的黑色山崖。
图传信号开端变得时断时续,无人机内置的电子罗盘,指针像喝醉了酒相同张狂地打着转。
就在这时,屏幕一角的信号频谱仪上,一个极端弱小的、简直能忽略不计的金属反射信号,忽然跳动了一下!
他瞳孔猛地一缩,也顾不上电量了,猛地推进摇杆,操作无人机朝着信号闪现的方向,强行下降高度,一头扎进了山沟里那片终年不散的浓雾之中。
范卫国低骂了一句,心都凉了半截,这要是失联了,他这台宝贝疙瘩可就告知在这了。
几秒钟后,就在他认为飞机现已撞山的时分,雪花状的屏幕,奇迹般地,又康复了明晰。
它的机身多半被藤蔓和苔藓掩盖,和周围的环境简直融为了一体,但那巨大的机翼和机身上依稀可见的“西南航空”四个字,都在向他宣告着它的身份。
电话接通后,两个加起来快一百一十岁的老男人,谁都没有说话,只能听到互相沉重的呼吸声。
由于他们心里都清楚,仅凭一段含糊的视频,和一段来源不明的“鬼信号”,没人会信任他们,更不会有谁乐意为了一个三十年前的悬案,派人来这种叫天天不该叫地地不灵的绝地送死。
这老猎人是本地的山民,一辈子都在黑龙山里打转,哪儿有坑哪儿有坎,比活地图还清楚。
这小伙子刚从地质大学博士结业,满脑子都是科学理论,胆子大得能包天,一传闻要去探秘“鬼飞机”,振奋得嗷嗷叫,连夜就背着他那些八怪七喇的勘探设备赶了过来。
他们瞒着各自的家人,以“进山进行地质勘探”为由,开着范卫国那辆破皮卡,一头扎进了黑龙山脉的深处。
他们只能靠着熊振山手里那张发黄的兽皮地图和最原始的指南针,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困难穿行。
一路上,毒蛇、蚂蟥、能把人困死的瘴气,无时无刻不在应战着他们软弱的神经。
陆晓川的各种高科技探测仪,在这里全都变成了一堆废铁,指针不是张狂乱转,便是爽性不动。
第五天的傍晚,在熊振山崴了脚,姜启明差点掉下山崖之后,这支狼狈不堪的部队,总算,抵达了那个被浓雾笼罩的山沟。

它像一座来自上个世纪的巨大纪念碑,被时刻忘记,被国际扔掉,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、凄凉而又怪异的气味。
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“咯吱吱”的金属歪曲声,那扇好像古墓进口般沉重的舱门,总算被撬开了一道能容一个人钻进去的缝隙。
一股严寒的、似乎被封存了三十年的空气,从门缝里猛地喷了出来,吹得几个人一颤抖。
,火狐体育下载app